東晉名士王述是個(gè)急性子,一言不合能跟雞蛋干上一架。他有次吃雞蛋,想用筷子戳起來,未能如愿,便怒不可遏地把雞蛋摔到地上,不料雞蛋還是完好如初。他抬腳便踩,又未踩中,因而怒槽全滿,撿起雞蛋放入口中,狠狠咬碎,然后憤然吐出,這才覺得出了惡氣。

王述出身于晉陽王氏,在東晉做到衛(wèi)將軍、揚(yáng)州刺史,后又入朝擔(dān)任尚書令。他的暴脾氣,在講究從容淡定的東晉名士看來太不講究了。得知王述和雞蛋打架,與他不大對(duì)付的王羲之說他沒一點(diǎn)值得稱道的地方。
才能不算出眾、性格又不大好,但王述在圈子里還是有一席之地的,因?yàn)樗谎b。
魏晉風(fēng)度傳至東晉,做作的成分越來越多。比如王獻(xiàn)之,房子起火了還不急不慢,叫了隨從擺足架勢(shì)才優(yōu)哉游哉地往外走。東晉名士好談歸隱,其實(shí)大多只是借此賺取名氣而為仕途鋪路,一旦被授予官職,還要裝作勉為其難地出山,然后謙讓一番,讓吃相不那么難看。
王述可不一樣,一點(diǎn)表面文章都不做。兒子王坦之擔(dān)心他這樣會(huì)招來負(fù)面評(píng)價(jià),在他被任命為尚書令時(shí)勸他適當(dāng)謙讓一下。王述問:“你覺得我配得上這個(gè)職務(wù)嗎?”“當(dāng)然,不過謙讓是好事。”王述很不高興地說:“既然配得上,何必假意去讓?”
東晉時(shí)的郡守、縣令雖不在朝,卻是油水充足的肥差。王述早年因錢不夠用,便請(qǐng)求去宛陵當(dāng)縣令,任職期間大肆收錢,置辦家產(chǎn),后來被舉報(bào)了。掌權(quán)的王導(dǎo)向來優(yōu)待士族,執(zhí)政風(fēng)格又是“網(wǎng)漏吞舟”,自然不會(huì)把王述怎么著。不過既然州里已把這事擺到臺(tái)面上,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找王述談話,象征性地給予批評(píng)教育,“你是名門子弟,將來不憂富貴,現(xiàn)在自降身份去小小一縣求財(cái),不太合適。”王述滿不在乎地回答:“我有分寸,如果覺得錢夠了自然不會(huì)再收。”

東晉盛行清談,王述卻不愛說話。參加聚會(huì)時(shí),別人激烈辯論,他則冷眼旁觀,冷不丁插上一句話,卻足以改變整個(gè)氣氛。王導(dǎo)有次組織聚會(huì),每次他發(fā)表看法,在座的人都紛紛點(diǎn)贊,氣氛很是歡樂,不料王述正氣凜然地說:“他又不是堯、舜那樣完美的人物,怎么可能說什么都是對(duì)的?”
這樣的行事風(fēng)格,恐怕不大受人歡迎。不過王述直來直去,不用費(fèi)勁猜他的心思。王述嫌棄桓溫門第不高,不同意王坦之嫁女給桓家,王坦之不敢直說,只好用其他理由婉拒。桓溫一眼就看穿了,說:“不用解釋,定是令尊不愿意。”
所以,王述雖被稱贊清簡(jiǎn)剛正,但不夠曠達(dá),不討人喜歡。不過,朝廷需要這樣的人來處理大事。
隆和元年(362年),桓溫提議遷都洛陽,把東晉君臣嚇壞了。正在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時(shí),王述說:桓溫不過是虛張聲勢(shì)、恐嚇朝廷而已,只管聽他的,他肯定不會(huì)真的這么干。于是朝廷同意桓溫所請(qǐng),還勉勵(lì)了他一番,把球踢給他,遷都一事果然無疾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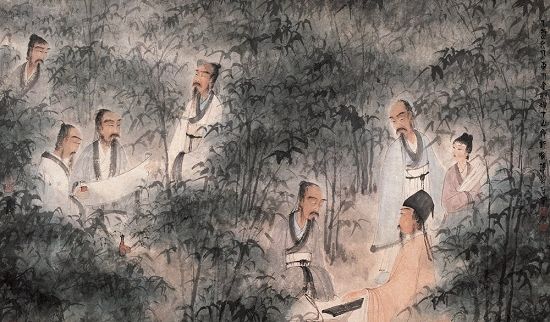
這樣一個(gè)我行我素的人,在官位顯貴后居然重視起名聲了。謝奕性子粗鄙,曾因?qū)ν跏霾粷M而當(dāng)面大罵。王述沒有針鋒相對(duì),只是面對(duì)墻壁任他發(fā)火,直到他罵夠了離開后才歸坐。一點(diǎn)就炸的“火藥桶”,居然變成了罵不還口的“棉花團(tuán)”,簡(jiǎn)直像個(gè)假王述。他努力把自己往名士推崇的雅量上靠,雖得到了好評(píng),卻顯得有點(diǎn)裝,反而不如之前那個(gè)“真俗人”。




請(qǐng)輸入驗(yàn)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