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認為,仇英的畫是“雅”而有士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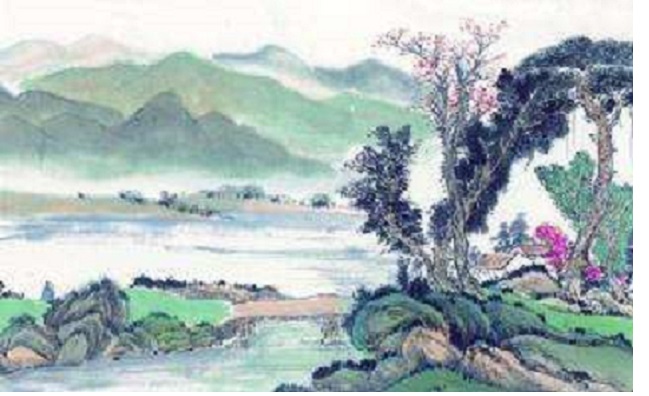
在文人畫家統治下的畫壇,似乎從來就輕視畫工。明末畫壇評論大佬董其昌著書立說,以“南北宗論”將仇英歸為了貶抑行家畫的“北宗”一派,但看到仇英的精工細筆,董其昌也默默豎起了大拇指,稱仇英為“近代高手第一”,“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被仇英的畫所折服。于是乎,董其昌也糾結了,而后的大批文人學者,直至現代美術史的研究,也受到影響,眾說紛紜,對仇英的評判褒貶不一。
仇英在人生中最輝煌的時刻,“行年五十”早早去世了。在他死后,董其昌立足于“南北宗論”的基礎上,將仇英歸于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水的“北宗”一路。也就是說,由于“南北宗”理論所造成的文人畫家和職業畫家的二分法,在該體系中,仇英只能被歸于“其術近苦”的“習者之流”。從而也開始了仇英身份的討論以及繪畫的風格分類的長期爭議。
董其昌認為,仇英的畫是“雅”而有士氣的,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與明四家其他三家并列的話,其他三家是文人畫,能夠與他們并列,也是屬于文人畫的范疇,因為,他里面的趣味還是雅的。仇英的畫風分為好幾個路數,學習二趙的大青綠風格,也有學習文徵明小青綠風格的影響,而這本身就是文人畫。為什么把仇英放在北宗里面?董其昌是一個有雄心的文人畫家,他要創立一種自己的繪畫理論,要立就不得不去破。
正是這種“不立則破”的心態,使得董其昌“鬼使神差”般的把仇英劃入到北宗體系中,對于這種體系的劃分,已經過世的文藝理論家王朝聞先生也曾經有過表述:“唐寅與仇英,與沈,文并稱‘吳門四家’,但兩人的藝術淵源都出自南宋院體,均師屬院體系統的職業老畫師周臣,其成熟畫風具有濃郁的行家氣息,因此,他們兩人難以歸入‘吳門畫派’,但有些畫史將二人歸入‘院體派’也不恰當”。幾百年之后,我們尚且有著不同的看法和感覺,更何況當年的董其昌。
一個歷史人物的形象,是后人不斷加工,通過文學等各種方式的闡釋,最后形成一個人物。我們現在知道的董其昌,不一定就是真實的董其昌,仇英也一樣。仇英的形象是董其昌來塑造的,因為他的言論影響大,起著最關鍵的作用。重新建構過去的歷史時,必然會牽涉到個人主觀的價值判斷。
“董其昌的南北宗論之于仇英的影響,使得很多近現代的學者所寫的中國繪畫史,或者藝術史,認為仇英是工匠、人物畫家、摹古高手等等,他們就對仇英做了另一方面的塑造,也可以說,這些負面的出發點,是來自于董其昌對北宗畫的批判。
董其昌扛了南北宗論這面大旗之后,后人受到董其昌的影響的也很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因為附和董其昌,導致走過了頭,一味批判仇英。比董其昌稍后的李日華,就提出了仇英繪畫品格不高的說法。他認為仇英臨摹功力達到了高水平,但還沒有參透古人的意趣。仇英可以做到繁密而不能做到簡淡,所以稱不上是高品。明代文學家陳繼儒曾經贊美仇英的《子虛上林圖》為第一,但還是把他的其他作品同于工匠畫,只能稱其為能品,在畫格上做了區分。
在繪畫創作中,文人畫家追求的是平淡天真與筆墨韻味,而仇英這類的職業畫家,卻以繪畫技巧的完備為宗旨。它甚至成為文人畫與畫工畫的分歧所在,職業畫家以畫畫為謀生的職業,而文人畫家則以畫畫為“寄興游心”、“聊以自娛”的筆墨游戲。正是這樣的區分以及董其昌的官方評判,使得仇英在傳統美術史上的認知遭到了“誤讀”。
仇英為什么最終“選擇”成為職業畫家?現在已經無從得知,但是,我們能從仇英留下的作品中感受到他的這種“徘徊”。因為,不管是哪個版本的《清明上河圖》,依舊是排隊的熱點。其實,仇英本的《清明上河圖》中已經少了很多的工匠氣息,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比較工匠性質的,而且顏色方面沒有那么鮮艷,覆色比較厚重一些。到了仇英這個年代,整個市民文化、商業文化發達,在繪畫方面表現出一種艷麗獨彩當然是艷而不俗。
仇本《清明上河圖》給我們再造了一個比北宋汴京更令人激動城市—蘇州。以郊外田園風光起,漸入街市,石橋上下,人群熙攘,運河兩岸,舟船貨運。熱鬧的蘇州市區,街道布滿“書坊”“南貨店”“描金漆器”“精裱詩畫”等各式的商鋪,還有迎親的隊伍和社戲的場面,河道繞綠瓦黃墻轉入城郊,以宮廷建筑及龍舟競技的場面結束畫面,而這繁華的蘇州城正是仇英身在的市井街頭。
而在《桃源仙境圖》、《蓮溪漁隱圖》以及《楓溪垂釣圖》等山水圖軸中,則呈現出了仇英另一個精神世界。以“秀雅纖麗”的院體風格著稱,而在華貴富麗中又蘊含著濃重的文人情趣,與文人畫家的書齋山水在情調上有相合之處。《赤壁圖》一改他嚴肅的畫風,取法馬遠,只畫一角山石、一夫一童一樹,淡墨遠山,一派文人高士超然世外的風采。仇英在這些作品中透過清麗爽朗的畫面,有側重文化上的匠心的追求,最大限度地凸現了他的追求文人廟堂的雅逸理想。
在仇英的思想或趣味上,或多或少與一般民眾乃至新興市民存在著聯系,具有與世俗相通的審美情感,但是,他沒有沽染上太多明清文人教條式的程式化的習氣,他的作畫態度可能達不到真正的南宗文人畫家瀟灑放達,但絕非否定他不“以畫為寄”。加上吳地濃厚的文人藝術風氣的熏染,使他的繪畫融入了文人畫的意趣,雖身為職業畫家,但其作品中所透露出的“士氣”,代表了當時融合院體與文人畫風的另一類型的風尚。
仇英沒有讀書取仕,也就沒有機會去品嘗唐寅那樣多大起大落的仕途遭遇,簡單的畫工生活使他有充足的心理空間去執著追求自己偏愛的繪畫事業,但也因此缺少了唐寅那種由坎坷際遇促成的靈性而產生的瀟灑。仇英出身低下,卻對清雅高尚的文人畫風產生了一種“圍城”般的渴望。也許,得到文人群體的贊揚與推薦,也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他內心身份的缺失。而極為認真的作畫則更多表現出來是出于自身對真實興趣和愛好的選擇,可以說,仇英擁有更純粹的藝術態度。
我們從明代繪畫史上看,不乏一些介于職業畫家和文人畫家之間的畫家,如與仇英同時的謝時臣、晚明的藍瑛。明代,文人畫家和職業畫家本就互有交往,在文人畫派逐漸占據畫壇主流時,職業畫家難免也受其影響,有時并主動向其靠攏,造成文人畫家和職業畫家的合流趨勢。從而也使得藝術史對于藝術流派的性質和畫家個人身份的界定顯得左右為難。董其昌雖將仇英劃入“北宗”,卻仍有保留,對于唐寅這樣行利兼有的畫家則干脆回避。而藝術風格介于浙派、吳派之間的謝時臣,由于無法被歸入南北宗之任何一派,幾乎成了藝術史上的“失蹤者”。




請輸入驗證碼